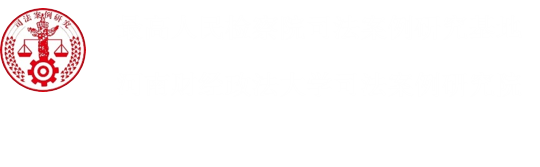作者简介:
刘夏,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
作为正当防卫的经典案例,“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对我国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刘海龙的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正在进行”是该案认定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有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能够进行正当防卫;事先防卫与事后防卫都属于防卫不适时,不能成为排除犯罪的事由。根据相关视频资料与警方的《通报》,于海明与刘海龙的系列攻防行为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首先,刘海龙先后徒手攻击、从汽车中拿出砍刀攻击于海明;其次,刘海龙砍刀脱落,于海明在争抢中夺到砍刀,对刘海龙连砍五刀;再次,刘海龙向汽车跑去,于海明在追击过程中连砍两刀;最后,刘海龙倒地不起,于海明停止攻击。没有争议的是:在第一个阶段,刘海龙已经实施了不法侵害行为,于海明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最后一个阶段,随着刘海龙重伤倒地,其可能攻击的危险性已完全消失,于海明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值得讨论是中间两个阶段:在第二阶段,随着砍刀脱手,刘海龙丧失了对凶器的控制权,此时是否表明不法侵害已经停止?在第三阶段,刘海龙已经逃跑,没有继续进行攻击,是否也意味着不法侵害的停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于海明就属于防卫不适时,应当以犯罪论处。对此,检察机关在《通报》与指导案例中进行了解答,并在整体上提出了“正在进行”的判断标准,从而肯定了于海明进行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要件。接下来,笔者将围绕该指导案例,从不法侵害的起止时间入手,围绕“凶器脱手”与“追砍”两个核心事实展开讨论,以期从法教义学角度对指导案例中的规则进行提炼,从而归纳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判断标准。
一、“正在进行”的判断基础
(一)“行为说”之否定
我国通说认为,“正在进行”指不法侵害正处于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进行阶段。在具体解释中,不少学者主张根据不法侵害行为的具体样态予以认定,即将着手实施侵害行为作为不法侵害的始点,将行为实施完毕作为不法侵害的终点。亦即,只有达到了典型构成要件行为之前的密接行为时点,并且尚未实施完成时,不法侵害才属于“正在进行”。毕竟,正当防卫权是一种“凌厉”的武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限定,以免过早使用,如此方能避免权利滥用、侵害他人利益。如周光权教授就明确指出:“不法侵害的开始,和实行行为的‘着手’是大致相同的概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5)犯罪行为已经既遂或者实害结果已经发生。”
但是,将行为作为判断基础、尤其是以构成未遂犯作为正当防卫始点的观点不但混淆了犯罪形态与不法侵害的规范理由,也不足以周延地保护防卫者。从规范意义上看,正当防卫并非刑罚的替代品,更不是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授予公民临时行使的刑罚权,故对不法侵害的判断不需要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承担刑罚为依据。正如本指导案例所指出的,“判断标准不能机械地对刑法上的着手与既遂作出理解、判断,因为着手与既遂侧重的是侵害人可罚性的行为阶段问题,而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侧重的是防卫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从起点角度而言,出于保障人权、科学限缩犯罪既遂范围的考虑,犯罪未遂的界限应当尽可能靠近既遂,对危险紧迫性的判断相应也更为严格。但正当防卫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是“正对不正”的较量,故不应进行过分限制。并且对于部分严重的暴力犯罪,如果等待行为人着手实施犯罪后才进行防卫,往往已经十分困难、甚至无法有效防卫。例如,不可能要求被害人等到对方持枪瞄准后方可防卫。因此,以着手实施侵害行为作为正当防卫的起点将导致防卫时机过迟,不利于法益保护,故有必要将开始时间前提。从终点角度而言,部分侵害行为即使实施完毕、甚至达到既遂状态后,也仍然存在能够挽回不法侵害所造成损失的状态,如针对财产犯罪的追击行为;或者侵害人还有继续攻击或再次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此时,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允许其实施正当防卫。
(二)“法益说”之提倡
国家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赋予个人保护法秩序的机会,通过正对不正的较量,恢复被侵害的法秩序,保护无辜者的利益。因此,与保护法益的关联性是决定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核心要素。如果虽系与侵害者的对抗行为,但与保护法益无关,就不能被评价为防卫行为。例如,在他人故意将汽车挡在自家门口的情况下,将汽车轮胎扎破、车窗打碎的行为;或是当侵害者驾驶汽车飞速撞向他人时,对其射击的行为,由于均无法消除法益被侵害的状态,故均不能构成正当防卫。因此,在判断防卫时机时,也应围绕“法益”这一核心要素、而非侵害行为本身的实施样态展开。只要侵害行为在客观上将法益处于较为紧迫、明显的危险之中,即使尚未着手实施,也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相反,如果法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或威胁之中,或是已经被彻底损害而失去挽回的余地时,就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因此,法益的紧迫危险性与现实侵害性是决定不法侵害起止时间的核心要素,只要具备该要素,就可以认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正如本指导案例说指出的:“不能要求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加诸被害人身上,只要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已经迫在眼前,或者已达既遂状态但侵害行为没有实施终了的,就应当认定为正在进行。”
那么,在起点的判断上,究竟何种侵害行为会导致“现实危险已经迫在眼前”,或者如德国通说所认为的“迫在眉睫”呢?对此,主要存在“有效说”“具体危险说”“预备行为最后阶段说”等学说的对立。笔者认为,“具体危险说”的判断标准较为模糊,更多体现为一种指导思路;“有效说”则可能会失之过宽,将“正在进行”的始点大幅提前,必须予以适当限制。相较而言,采取“预备行为最后阶段说”更为合理,即以侵害着手实行之前、且紧邻于密接行为的预备行为的最后阶段来确定不法侵害的开始时点。此时,不法侵害也已经到达了防卫者能够有效防卫的最后时点。如果再拖下去,就很可能难以实现防卫目的,或是必须承担较大的风险——如果非得冒着极大风险才能保护法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又有多大意义呢?例如,行为人正将手伸进口袋,准备掏出一把上膛的手枪。虽然此时还尚未着手,但已经进行到预备阶段的最后一步;只要将手枪掏出,就会立刻实施不法侵害行为。此时,被侵害人就可以直接进行反击,而无需等到对方掏出枪后再进行防卫。再如,倘若本案中刘海龙拿着刀走到于海明面前,正欲实施侵害时刀从手中脱落,刘海龙随即弯腰去捡。此时虽然尚处于犯罪预备阶段,但一旦其将刀捡起,就会马上着手实行侵害行为。因此,抢刀是预备行为的最后阶段与最终时点,构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面对这一情况,于海明自然也可以与刘海龙争抢,并进行正当防卫,而不必非得等到刘海龙对自己刺出一刀后才能进行防卫。当然,如果某一犯罪的预备行为已经构成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则不必等到最后一步才能进行防卫。例如,入户虽是入户盗窃的预备行为,但非法侵入住宅行为本身已属犯罪,故被害人完全可以在对方撬门开锁时进行防卫。再如“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检例第46号)中,朱凤山早在齐某攀爬自家院墙时就可以进行防卫,而其直到齐某跳入院内与自己撕扯时才进行防卫,无疑满足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在终点的判断上,我国通说以不法侵害的停止、防卫起因消失作为判断的重要节点与决定性依据,虽然在理论上能够自洽,却给当事人提出了过高的标准,也不符合法益保护这一立法目的。在以法益侵害为判断基础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认为只要侵害人的侵害举动停止,就不能再实行防卫;而应判断这种停止是暂时的还是终局的,不法侵害是否会马上继续进行,被破坏的法益能否即时恢复。只要法益处于被侵害的过程中或仍存在被侵害的高度危险,就可以实行防卫。以盗窃罪为例,盗窃行为的实施完毕并不意味着侵害者对赃物建立起安全稳定的支配关系,只要被害人当场进行追击,其财产法益仍处于被侵害的过程中,故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只有当不法侵害已经不可能继续侵害或威胁法益时,如攻击者逃离、丧失行动能力、被防卫者制止、不法行为基于主客观因素已不能继续进行等情形,或者法益已经被彻底侵害,如被害人已被杀死、侵财者携带赃物逃脱等,才能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二、“正在进行”的判断标准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正当防卫的认定中,是否存在不法侵害与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其实是两个问题——前者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性要件,后者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要件。“是否存在”解决的是不法侵害有无的问题,而“正在进行”则是在肯定了存在不法侵害的前提下,判断该侵害是否足以造成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从而到达应当进行正当防卫的阶段。在认定是否存在不法侵害时,无疑应当采取客观标准,即从事后(审判时)的视角进行回溯,在客观上加以判断。如果客观上并无不法侵害,行为人却因为恐慌、紧张等心理,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的,则应以“假想防卫”论处——符合过失成立条件的,构成过失犯罪;不具有过失的,则属于意外事件。
因此,本部分内容旨在讨论在存在不法侵害的前提下,究竟由谁判断是否存在紧迫的、尚可挽回的法益侵害的问题。对此,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等多种学说的对立。笔者认为,应当以修正的客观说为判断标准,并且针对行为始点与终点有所区别。理由主要在于:
第一,主观说的判断标准过于模糊。毕竟,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与否不能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臆测,而是需要综合客观事实进行具体认定。倘若采取防卫者的视角,将无法排除行为人在主观上判断上具有过失甚至重大过失的可能性;如果判断错误,就很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暴力行为,从而造成无辜第三人伤亡等严重后果。因此,这一角度将使法律的客观功效出现漏洞,相当于在事实上赋予行为人无限制的防卫权,是法治国所不能允许的。
第二,纯粹的客观说亦不合理。如果以全知全能的事后视角,基于全部案件事实判断不法侵害是否事实上“正在进行”,不但难度极大、要求过高,也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一方面,在多数情况下,准确判断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引发防卫行为的冲突往往不是瞬时发生的,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矛盾、口角、推搡等行为逐渐升级而成的,在从缓和到激烈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有停顿的间隙。有的不法侵害人虽然在表面上暂时停止了侵害,却暗中为下次攻击积蓄力量、寻找更有利的机会。因此,这种“停顿”究竟意味着冲突的结束,还是下一步爆发前的短暂平静,即使旁观者清的法官也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更遑论当局者迷的行为人了。如果非要以攻击者的自证来认定不法侵害是否停止,就将使这一判断标准过于主观化,也不利于无辜被害人的法益保护。正如车浩教授所言,面对危机状况时,就如同进入了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此时,更应当适用战争规则而非公平竞赛的比赛规则。如果要求被攻击者必须准确判断不法侵害的结束时点,只要攻击者“喊停”,自己就非得罢手,无疑将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攻击者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而无辜者则一直陷入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除了攻击者受伤倒地等特殊情况外,不法侵害是否停止的主动权完全取决于攻击者,被害人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判断——尤其是在仓促应战、自身面临巨大危险、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在正当防卫的另一经典案例“涞源反杀案”中,检方就明确指出:在黑夜被人侵入住宅行凶的紧急关头,防卫人由于惊吓而精神高度紧张、心理极度恐惧,显然难以准确判断入侵者倒地后是否会继续实施侵害行为。因此,要求防卫者对不法侵害是否停止进行准确判断的观点属于一种鼓励攻击、限制防卫的思路,明显不符合“正义不必屈服于不正义”的理念,不利于保护防卫者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也没有必要对防卫人的主观判断提出过于严格的要求。在特殊预防层面,即在客观上超过了防卫的时间限度,但防卫者之所以实施反击行为,主要系出于防卫而非报复的需要,仍是一名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公民,并未明显偏离法秩序的轨道;况且只要失去了特定的情境,其就不太可能再实施这类行为。而在一般预防层面,由于这种情况缺乏“可复制性”,一般人难以效仿;即使施加处罚,威慑力也十分有限。此外,如果对时间要件的认定过于严苛,不法侵害者的犯罪成本就将大幅降低,其可能会抱着赌一赌、甚至将防卫者拉下水的心态去尝试不法行为。此时,被害人为了避免因对时间界限把握不准而被法律惩罚,大多只能选择退让而非反击,这就更加助长了侵害者的嚣张气焰。如此一来,立法者所意图起到的预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从一般人的视角出发,进行事中判断。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判断视角的一般人并非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类具有相似特点、事实上“不一般”的人群的集合,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判断一般人会如何行动时,必须结合当事人的体质、性格、智识、经验、弱点以及具体的时空条件进行综合考虑,而绝不能仅凭置身事外的我们的第一感觉进行判断。我们可以坐在电脑前反复查看相关资料,分析哪一刀正当,哪一刀过当;但在危急情况下,一般人能否进行如此冷静的思考呢?即使不能确定当事人的确切想法,但只要存在合理怀疑,也应秉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关于是否存在危险的判断予以肯定。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两高两部关于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并赋予了防卫人一定的“误判特权”,而不苛求其做出不合情理的判断。
第四,与不法侵害的开始阶段相比,在侵害的持续阶段,对侵害是否仍具有“紧迫性”、是否结束的判断理应更为缓和。理由在于在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开始时,由于急迫不正的侵害尚未全部展现,故此时侵害者与被害人的处境尚未处于失衡状态,双方的法益理应得到较为平等的保护,并无高下之分。而不法侵害一旦开始,双方的地位将导致攻击者法益的值得保护性下降,此时再考虑防止正当防卫的滥用就未必是妥当的,故可以宽泛地认定侵害的急迫性。此外,在对始点判断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无论在不法、责任还是预防层面都与防卫过当不具有可比性,最多只能以假想防卫论处。而在对终点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则与防卫过当有较多相似之处,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为“量的防卫过当”。因此,对不法侵害的始点与终点的判断标准理应所有区别,需要围绕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三、本案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具体分析
(一)凶器脱手与“正在进行”的认定
本案中,刘海龙虽因砍刀脱手而停止对于海明进行攻击,但这种停止只是暂时而非终局的。虽然不能排除其夺刀只是为了避免于海明将刀捡起后对自己实施攻击,并没有再次实施侵害行为的故意;但根据案情判断,这种概率应当微乎其微。自始至终,刘海龙都是一个积极的攻击者,从自行下车推搡、踢打于海明,再到从车中取出砍刀连续击打于海明颈部、腰部、腿部,不法侵害不断升级,明显表现出其极强的不法侵害意识;而于海明在夺刀前也一直在进行防御,直到被打了六七下后才真正地开始还手。寄希望于刘海龙在抢到刀后瞬间清醒并彻底放弃攻击意图,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争抢砍刀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还具有继续攻击的想法——如果其在砍刀脱手后立即回避,或许会成为认定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关键证据。前文已述,对侵害持续阶段“紧迫性”的判断不宜过严,行为人前期的不法侵害是其继续侵害或威胁法益的有力征表,对实施后续行为可能性的判断无需达到盖然性的程度。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刘海龙在砍刀脱手实施争抢行为,具有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高度可能性,表明不法侵害仍然继续,于海明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对此,警方的《通报》中明确指出:“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刘海龙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抢刀。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检方的《通报》也认为,刘海龙在砍刀甩落在地后,立即上前争夺,表明其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笔者对上述观点表述赞同。
(二)追砍行为与“正在进行”的认定
在本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于海明追砍刘海龙的行为进行定性。有观点认为,在刘海龙逃跑之后,其对于海明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而于海明仍然持刀追砍,已经不具备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尽管于海明之前的反击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其后续追击行为也将构成故意犯罪。虽然在本案中,于海明的追砍行为在事实上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对刘海龙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也不符合相关犯罪构成;但如果这两刀砍中了刘海龙,且对其造成了伤害,又将如何处理?毕竟,在类似案件中,追击者不可能总是这么“幸运”。对此,本指导案例明确指出:“判断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应看侵害人是否已经实质性脱离现场以及是否还有继续攻击或再次发动攻击的可能。”显然,其采取的是整体判断思路,认为于海明在实施后续追砍行为时,刘海龙的不法侵害状态仍在延续,即使后两刀砍中刘海龙,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具体而言,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于海明在受到侵害后,心理上已经处于紧张、惊讶、恐惧的状态。警方在讯问时提问:“你觉得他要把你砍死是吧?”于海明回答:“是,死了,朝我后面那么一下,脑子里嗡了一下,感觉就死了,跟做梦似的。”“就拿刀挥他,当时感觉人跟疯了一样在那里。”直到同伴把自己死死抱住之后,才逐渐恢复了理智。从上述细节不难看出,于海明在当时处于责任能力降低的状态,并非有些网友所认为的“冷静的反杀者”。其次,于海明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刘海龙向车子逃去,危险状态也没有完全消失。刘海龙在被砍伤后,并没有马上陷入丧失侵害能力的状态,反而马上爬起,甚至还一度与于海明对峙。其逃跑的方向也指向汽车,而不是其他空旷场所。对此,检方《意见》明确指出,刘海龙在受伤起身后,立即跑向原放置砍刀的汽车,由此可知,于海明无法排除其从车内取出其他“凶器”的可能性。兼之刘海龙随身携带管制刀具,态度蛮狠、粗暴、上半身布满凶兽纹身、佩戴夸张的金链子,符合当时济南公安机关公布的黑恶势力的29种外在表现。基于这种大众的符号化认识,于海明有充分的理由误以为刘海龙是凶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可能会继续实施不法侵害。最后,于海明对刘海龙的防卫与反击行为均发生在短短的十几秒内,地点也未发生变化,始终在宝马车的周围,二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如警方所言,可以被评价为“一个连续行为”。综上所述,防卫与追击都是于海明在紧要关头所实施的求生行为,未超出防卫时机,在整体上均具有防卫性质。
根据本案,我们可以尝试提炼出在侵害人停止攻击后,不法侵害是否终局性停止的若干判断规则。第一,侵害人是否存在再度攻击的危险。倘若存在凶器还在现场、停止侵害者还具有一定的反抗能力、有再度攻击可能等情形的,出于免受二次侵害等考虑,仍应允许被侵害者继续实施防卫行为。反之,如果侵害人已经退却并离开原地,其侵害法益的可能性自然大幅降低。此时防卫者再进行追击的,原则上就不再满足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要件,但仍有符合扭送等其他违法阻却事由的余地。例如,攻击者在攻击后躲藏到自己的房间内,并关上房门,这足以表明其主观上的退让意思,没有再实施不法侵害的危险。被攻击者仍然破门而入,向对方胸部刺戳的,无疑应否定后续行为的防卫性质。再如,攻击者在关公刀掉落后驾车逃跑,也能够明显反映出其已经放弃了不法侵害,而被攻击者捡起刀后驱车追赶,将其逼下车后进行砍杀的,自然也不具有任何防卫因素。
第二,不法侵害停止的时间长短。在不法侵害刚刚停止的情况下,防卫者由于之前被侵害引发的精神高度紧张,确实难以准确判断防卫时间的界限。但如果已经停止了较长时间,就给防卫人留下了冷静思考的余地,其因遭受侵害而产生的恐惧、紧张心理也会逐渐消散。此时,如果仍主张侵害者具有再次侵害危险而实施反击行为的,就不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现场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侵害人。在参与者众多的场合下,即使不法侵害人停止了攻击,与其身处同一阵营的观战者却仍有接续实施侵害行为的可能,故不能仅以先动手者的罢手作为不法侵害停止的唯一判断标准,还需要综合考量他人因素。如在本案中,现场还有一名与刘海龙同车的人员,并在最初与于海明进行过争执,属于事端的挑起者。他的存在势必会对于海明关于危险结束与否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但无论如何,与侵害者无关的第三人并未引发防卫者的紧张情绪,无需为此负责。如果防卫者对他们进行“反击”的,就已经逾越了攻击者的权利空间,侵犯到无辜第三人的权利空间。此时,应当视情况成立假想防卫或构成相应犯罪。
最后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借鉴德日相关理论,提出了“量(时间上)的防卫过当”概念,并认为本案就是典型代表。无疑,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与“量的防卫过当”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只要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行为人就不可能成立量的防卫过当;只有一般人认为不法侵害事实上已经结束,而行为人由于紧张、恐慌等原因对防卫时机出现认识错误,从而逾越了时间界限时,才可能成立量的防卫过当。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尽管于海明前后实施的防卫与反击行为能够被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但结合案件当时情境,认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的观点更为合适。因此,本案尚无需援引量的防卫过当理论。当然,量的防卫过当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其具体适用条件与典型案例,值得我们今后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策划、审核:侯东亮
编辑:刘俊拴
校对:侯慧娟
(声明:本文纯属学术交流,拒绝任何其他应用目的。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基地,我们将及时予以处理)